2020年看过的两本好书
渡过这混乱的一年,在看过的书中挑选出这两本好书。
2020 年真是难以忘怀的一年。记得年初回到家,仍觉得是寻常的新一年。之后疫情不断升级,也逐渐适应了线上的授课和工作。四月份和友人在街头散步,全城开始鸣笛哀悼,那一刻才恍然意识到:世界在这一年被永远地改变了。至于我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里也是按部就班符合预期,乏善可陈。所幸今年在大疫之中看了两本不错的书。
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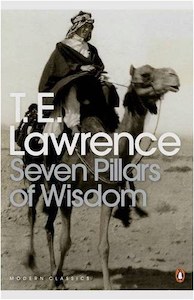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对于劳伦斯的事迹有了笼统的了解。真正吸引我去看他的自传的是战地一的「事在人为」关卡。「事在人为」的开头语如此:
阿拉伯沙漠。由飄砂與滾燙巨石組成的一片汪洋。在這些沙丘之下,蘊藏著黑色金礦石油。400 多年来,鄂圖曼帝国統治了阿拉伯沙漠,但鄂圖曼的統治並非從未遭到抵抗,一小股贝都因反抗军集結起來要推翻帝國。他們出手毫無預兆,並且出擊完就消失在沙漠當中。跟他們一同作戰的,還有一位英國軍官,他立下的功勛讓他有廣為人知的聲望。全世界的人都叫他——阿拉伯的勞倫斯。
实在是非常的个人英雄主义,激动人心。西方对于近代以前的人名有出身地加姓名的叙述方式,例如亚历山大港的丢番图(Dióphantos ho Alexandreús)、伊贝林的贝里昂(Balian d'Ibelin)这样,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酷的。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这个词赋予给一位英国上校,显然是为了体现出他对阿拉伯这片土地的重要性。这是旁人所观,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段经历又是如何呢?抱着这种心态我开始阅读《智慧七柱》。
相信大家对于殖民主义者的印象,可能是在某个维多利亚风格的豪奢雪茄室里,几个阴险的老绅士在阴暗的环境里一边抽雪茄一边在地图上瓜分世界。但《智慧七柱》展现了另一种殖民者的形象——年轻、博学、无畏向前。劳伦斯本身是研究近东及中东文化的学者,而且是相当古怪的nerd;同时他也是优秀的军事家,精通阿拉伯文化的背景让他可以更好的在这片土地上发挥。他开创了现代游击战的战术,书中后半部分很大的篇幅主要是谈他带领一小股人如何破袭奥斯曼帝国的铁路网,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不论是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是战地一的「事在人为」都很好地反映了他的作战方式——如同一位英勇的连长一样带着少量勇士神出鬼没,这与印象中的雪茄室阴谋家的形象完全相反——一言以蔽之,就是「给我冲」和「跟我冲」的区别。
这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如何让阿拉伯人信服一位来自英国的军官呢?我觉得电影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劳伦斯服众的论据不够充足,如果阅读《智慧七柱》,你会发现全书与其说是一本革命史或英雄的自传,不如说是一位冒险家记载的阿拉伯风物志;劳伦斯不但是一位牛津高材生和游击队长,还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者;即使对中东的景色和人文毫不了解,在他的笔下也可以很好的领略他看到的美好:山谷中壮丽的晚霞、绵延不尽的沙丘、阿拉伯人前文明世代的朴素习俗、烤骆驼篝火大餐等等。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劳伦斯是以一种平等乃至欣赏的态度面对阿拉伯世界的,他很欢快地穿上阿拉伯长袍、挥舞弯刀、接受阿拉伯人的饮水习俗;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行为是反殖民的,试想,一个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的模样是无法打入甚至带领一个贝都因部落的。他也对所见的弊端审视得非常犀利,贝都因部落的猜忌和愚昧也记录在本书中,正是这种前现代的部落组织体系让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一盘散沙。
还有一点感悟就是阅读本书会让人对中东的地理和地缘更加地了解。我自觉地理在中国人里面已经算是还不错的水准,但在阅读之前对中东的地理了解还是不够深——大概只是泛泛地知道红海在哪里、埃及在哪里之类的。《智慧七柱》中对汉志铁路的破袭战记叙颇多,我翻开地图详细看了汉志地区和内志地区的地理位置。人类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宗教经典和文学名著描写了中东地区的地点,阅读本书时你会不由得联想起这些无数次出现的地名,会把一盘散沙的记忆建立起联系:“为什么大马士革对阿拉伯人怎么重要?锡安(Zion)在哪里?原来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怪不得它是这么多宗教的圣城……”这样的感想在看这本书和不断翻阅地图之间此起彼伏,真的是很大的乐趣。
阿拉伯的劳伦斯改变了中东的格局,却也没有改变;他是一位传奇的英雄,却也不是。赛克斯-皮科协定最后推翻了他的革命成功,让他深感背叛。让人不由得想起一种论调:「技术/战术在战略下是无用的」,这种论调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去反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又是成立的,比如在劳伦斯上校身上,这让读者不禁感叹传奇英雄的末路。
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 :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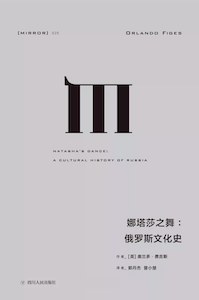
《娜塔莎之舞》是我看到副标题「俄罗斯文化史」之后就决定购买的。倘若是「法国文化史」或者「德国文化史」我可能就没有这种一瞬间的购买念头——相较于刻板印象中的欧洲文化,俄罗斯文化与其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但在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眼中,俄罗斯文化又是那样的具有异域情调,忧伤、欢愉、高雅、朴实……充满了具有张力的矛盾。本书的核心论点也在于这些矛盾是如何形成的:来自西方的欧陆文化与来自东方的鞑靼文化在俄罗斯相碰撞,正如出身贵族的娜塔莎在乡间无比自然地跳起农村的舞蹈。
彼得大帝的剧烈改革将俄罗斯从蒙古人统治的影子下拉向欧陆的文化,甚至不惜为了这个目的在一无所有的涅瓦河畔建立全新的首都圣彼得堡,避开莫斯科的旧势力影响实行全盘欧化。但原先的印记并没有因为彼得改革而完全褪去,它存在于俄国的乡间、田野、东正教教堂中,使得俄罗斯文化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显得格外特别。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写的:“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
本书很详细地描写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各项璀璨俄罗斯艺术的来源与发展,不论是芭蕾、画作、文学。同时还联系俄罗斯的历史凸显出这些文化诞生的必然性,例如《伏尔加河的纤夫》是列宾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创作的,这些故事牵扯上时代的背景就会显得格外宏大。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并非鞑靼或乡间的文化左右了圣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反而是知识分子主动走入乡间吸收原本属于本土的文化养分,他们在文化认同上产生了困惑,解开这个困惑的关键是走到俄罗斯的乡间,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如年轻的列宾离开都市来到伏尔加河畔、正如托尔斯泰散尽城市的家产去开拓自己的庄园。作者想强调的大概是:俄罗斯文化并不是先天如此,它的矛盾的魅力是人为塑造的,而后有意识地巩固并推销给东西方的,对于俄罗斯人本身,也是自己身份认同的最好解答。
也许本书最有意义的主题,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暧昧的、变动的关系。一些贵族曾经尝试桥接两个群体之间扩大的分歧,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尼古拉•谢瑞麦捷夫(Nikolai Sheremetev)与农奴的婚姻致使他被上流社会放逐而年轻的民粹派则在他们在 1874 年伟大的朝圣之旅中联合普通人民的努力上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其他人则更为成功:十二月党人谢尔盖•瓦尔贡斯基(Sergei Volkonskii)能够在;流放中把自己重新发明为“农民王”并用他改进当地农业实践的努力赢得了西伯利亚农民的最终。托尔斯泰,尽管在农业方面遭遇了失败,却在他生命中介的时候以他对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拥护和他对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攻击在普通民众中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拥护。然而也有一些俄国人拒斥像赶上的浪漫主义那样桥接分裂的努力。契科夫,他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在他的故事中把农民描述为毋宁说是“俄国灵魂的化身”以及社会的一些特定的道德教益的承载着的普通人。而高尔基则毫不隐藏地表达了他对他眼中的农民的落后的嫌恶。
本书当然不能避开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发展,在我看来也没能做到完全客观。但不妨碍作者用一个观点就概括和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和好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